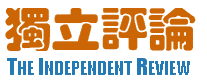
[PDF]
Untitled
观控相对论的信息范型(1) - 幸存者之家
survivor99.com/pscience/thesis/liuyuesheng1.htm
轉為繁體網頁
轉為繁體網頁
作者: 断章师爷
夏日杂谈(三)从薛定谔的猫说起2009-08-16 22:22:06 [点击:333]
夏日杂谈(三)从薛定谔的猫说起
断章师爷
上个月断断续续下了好几周雨,走过书架,总似乎闻到些幽幽的霉尘气。眼下骄阳炎炎。 小区内的左邻右舍都倾巢而出, 男女老幼皆躺在草地上享受日光。放眼望去,绿茵地上,彩伞林立,玉体横陈。不禁想起《世说新语》中西晋参军郝隆先生“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郝隆先生的书都装在肚里,所谓是“满腹经纶” ;我的书都插在架上,所以是“胸无点墨”。倘若我的所有书籍也象郝隆先生一样藏在肚中,那该多方便啊!只消挺着个鼓鼓囊囊的大肚子,潇洒地走到草地上,仰天八叉地在那儿躺上一阵,所有的霉菌和蠹鱼保管一扫而光。算了,还是回到我的书架边上来吧。
我的书架上有不少旧书,其中一册《科技德语文献》,是那种16开本的讲义,用蜡纸打字后翻印的,装订也很马虎。那还是我读硕士时修第二外语的参考资料。这本纸页泛黄的老讲义看是不会再去看了,却总舍不得扔掉,常会拿在手里摸挲一番,回想一下当年读此书时的情景,这大概也算是一种怀旧吧。
其实,这册外表不中看的讲义汇集了不少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等领域中的名家名篇,物理学方面的就有普朗克的演讲“Religion und Naturwissenschaft”(宗教和自然科学)、海森堡接受巴伐里亚天主教科学院奖时的发言“Wissenschaftliche wahrheit und Religion wahrheit”(科学真理和宗教真理)、泡利的书信“Wolfgang Pauli und C. G. Jung. Ein Briefwechsel”(泡利和容格的通信)等。第一篇“Schrödingers Katze”(薛定谔的猫)是从薛定谔发表在《自然科学》杂志上的那篇著名论文“Die gegenwärtige Situation in der Quantenmechanik”(量子力学的现状)中摘录下来的。
凡是读过物理学的人都知道薛定谔方程是量子力学的基本方程,其重要性就像牛顿定律在经典力学中的地位一样。 不过,话得说回来,薛定谔方程再重要,对之感兴趣的人毕竟只限于物理学圈内;薛定谔先生的那只猫却远远比薛定谔方程更惹人注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薛定谔先生这只半死不活的猫把物理学界闹得人仰马翻,直到现在还不得安宁。
薛定谔先生的猫是物理学史上有名的悖论(或者雅驯些称为佯谬)之一[1],他设计了一个思维实验(Gedankenexperiment):将一只猫关在钢制的密室中,室内还置有一小块放射性元素、一个盛有氰氢酸的玻璃瓶,以及一套受盖革计数器触发控制的、由锤子构成的执行机构。放射性元素不稳定,它会衰变放出一个中子,就此引发了相因的连锁反应,最终结果是锤子打破了室内的那个毒气瓶。事情很明显:如果放射性元素衰变了,那么毒气瓶就被打破,猫就被毒死;要是放射性元素没有衰变,那么猫就好好地活着。
根据哥本哈根学派的量子理论,没有测量之前,粒子的状态是模糊不清的, 取决于各种可能性的叠加结果[2]。(顺便插一句,量子态的叠加性和相干性正是未来的量子计算机和现行的经典计算机之间的根本差别。)也就是说未经测量的放射性元素处于衰变和不衰变这两种状态的叠加,只有确实地测量后才能随机地选择其中一种状态出现。原子核的衰变是随机事件,物理学家能精确测定的只是半衰期¾¾即放射性元素衰变一半所需要的时间。假定放射性元素的半衰期是一天,则过了一天,该元素就少了一半,再过一天,就又少了剩下的一半。但是物理学家却无法知道,放射性元素在什么时候衰变:上午,还是下午?当然,物理学家知道它在上午或下午衰变的几率¾¾也就是猫在上午或者下午死亡的几率大小。
即使不打开密室的门,根据日常的生活经验也可以断定,猫或者是死,或者是活,用量子力学术语来说这是猫的两种本征态[3]。如果用薛定谔方程来描述,猫处于一种死与活的叠加状态。只有在打开密室门的瞬间,才能确切地知道猫究竟是死还是活。这时表征猫的状态的波函数由叠加态立即收缩到某一个本征态,称之为波函数的“坍缩”(Kollaps)。
哥本哈根学派对于几率的诠释是:出现的结果只可能是唯一的一个,但是出现一个结果的前提是波函数必需坍缩。这儿想简单介绍一下何谓坍缩。一般来说,一个物理体系不会处于它的任何一个可观察量的本征态上。但是假如我们测量一个可观察量的话,其波函数就会立刻处于这个可观察量的本征态上。换句话说,某个体系与外界发生某些作用后,它的波函数会发生突变,变成为其中一个本征态或有限个具有相同本征值的本征态的线性组合。这个过程被称为波函数的坍缩。借助于Dirac符号,这一过程的数学表示非常简洁:一个用右矢(ket)表示的包含众多元素(本征态)的波函数仅相当于只含其中某一个元素(本征态)的右矢。但是波函数坍缩的真实性并没有被完全地确定;物理学家一直在争论,波函数的坍缩究竟是这个世界的自然现象之一,还仅仅只是属于某个现象的一个部份而已。为此,物理学家们不得不接受哥本哈根学派的诠释。这样做的代价是违反了薛定谔方程。这就难怪薛定谔先生一直耿耿于怀了。他挖苦说:“按照量子力学的解释,密室中的猫处于“死/活叠加态”——既死了又活着!要等到打开密室看猫一眼才决定其生死。”这儿薛定谔先生使用的动词不是发现(finden)而是决定(entscheiden),可见猫的命运竟然取决于人的观察!
对于物理学家来说,薛定谔先生囚禁猫的那个密室相当于潘多拉的盒子,释放出来的是永不消逝的灾难。一只活蹦乱跳的猫被关进密室后,既不能死,又不能活¾¾这显然是个悖论。数学计算的结果是二者的概率相等,也就是说这两种状态存在的可能性相同。那我们只能宣称此猫不死不活,或者又死又活。严谨的物理学世界被这只猫搅得周天寒彻,精确的物理科学成了一场猜谜游戏。难怪许多物理学家对此怒气冲冲,认为这只寻死觅活的猫简直亵读了科学的神圣。伟大的爱因斯坦先生对于薛定谔的猫也并不待见,他不承认薛定谔先生的猫的非本征态之说。因为他深信“上帝是不会掷骰子的”,认为一定有一个内在的机制组成了事物的真实本性。他花了数年时间企图设计一个思维实验来检验这种内在真实性是否在起作用,遗憾的是他没有完成这种设计就去世了。
正当物理学家们被薛定谔先生这只猫的死活折磨得苦不堪言时,薛定谔先生本人却挥一挥衣袖,悄悄地离开了密室中的猫,转而从科学的角度去思考生命的本质,很快写出了不朽的名著 《什么是生命?》(Was ist Leben? )。在薛定谔先生阐述生命的奥秘时,被他囚禁在密室中的猫依然生死不明。然而,物理学家们一如既往地为薛定谔先生这只猫困惑、愤怒甚至憎恨,以至于希望这只该死的猫“像恐怖电影那样从视线中消失”。
但是这只恶魔附身的猫并未因此消逝,在这个充满困惑的大千世界中留下不少足迹。薛定谔的猫几乎成了娱乐明星,常常和巴甫洛夫的狗作为搭档一唱一和地出现在剧本、音乐和漫画中。最露脸的那次大概是被《恐惧之泪》(Tears of Fears)这个80年代红极一时的乐队作为一首歌的标题进行演唱,尽管唱词是“薛定谔的猫在这个世界中死了” (Schrödingers cat is dead to the world)。
当然物理学世界,更是薛定谔的猫经常出没的场所。本世纪初,根据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J. R. Friedman等人在接近绝对零度的超导体环形电路中由几十亿对电子构成的超导流的实验中,两个宏观不同的磁通态分别相当于“死猫”和“活猫”,它们在环中反向流动形成的对称和反对称的叠加相当于一只由“死”和“活”叠加的薛定谔猫。与薛定谔最初设计的单个粒子相比,几十亿对电子绝对是天文数字,所以著名的《Nature》 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报导,标题是《薛定谔的猫现在胖了》(Schrödinger's cat is now fat)。2005年底,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所的D. Leibfried等人在《Nature》杂志上称,他们使6个铍离子在50微秒内同时顺时针自旋和逆时针自旋,实现了两种相反量子态的等量叠加纠缠,也就是“薛定谔猫”态。在量子计算中把一种与所有处于0的量子比特(qubit)和所有处于1的量子比特的叠加相同的状态称之为猫态。用数学式来表示,即所有元素为0的右矢与所有元素为1的右矢的加和。据有关专家称,“薛定谔猫”态不仅具有理论研究意义,也有实际应用的潜力。比如,多粒子的“薛定谔猫”态系统可以作为未来高容错量子计算机的核心部件,也可以用来制造极其灵敏的传感器以及原子钟、干涉仪等精密测量装备。
身残志坚的斯蒂芬•霍金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地坐着轮椅遨游在不见天日的黑洞中,孜孜不倦地探索着宇宙起源的奥秘。他试图合并量子理论与广义相对论,期望以此解释整个宇宙从诞生到演化的过程。但是薛定谔先生的这只猫始终是量子理论上空一片飘忽不去的乌云,时不时会扰得霍金先生心神不定。以致霍金先生在不少场合中咒骂过“一听到薛定谔的猫,我就去拿我的枪” (When I hear of Schrödinger's cat, I reach for my gun.)。当然罗,即使把枪交给霍金先生,他也无法扣动扳机,因为他周身上下只有大脑和一个手指可以活动。更好的办法,是找个场所将这只该死的猫藏匿起来。
话分两支,1957年普林斯顿大学一个不出名的研究生Hugh Everett III公布了一个他创立的理论。他假设所有孤立系统的演化都遵循薛定谔方程,波函数不会坍缩,而量子的测量却只能得到处于叠加态的一种结果。Everett认为测量仪器与被测系统的状态之间有某种关联,称之为相对态。Everett表示,根据他的理论,测量带来的不是波函数的坍缩,而是一个分裂(Splitting)的宇宙。宇宙像一个阿米巴虫,当电子通过双缝后,虫子自我裂变,成为两只几乎一模一样的变形虫。唯一的不同是,一只虫子记得电子从左而过,另一只虫子记得电子从右而过。这样,薛定谔的猫再也不必为死活问题困扰,宇宙分裂成了两个,一个有活猫,一个有死猫。遗憾的是,整个物理学界对Everett的相对态异常冷漠。1959年Everett飞去哥本哈根叩见玻尔,后者却不作任何评论。心灰意冷的 Everett 退出物理界,任职于国防部五角大厦,后来又创办Lambda公司,成了一名资产亿万的私营承包商。
然而,冷灰中爆出了热栗子。1968年北卡州大学的量子权威Bryce S. DeWitt对 Everett 的假说给出了更为清晰的表述。DeWitt认为在测量过程中,由初始波函数描述的世界分裂为许多个相互不可观察但同样真实的世界分支,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对应于整个系统叠加态中的一个确定的成员态。这样,Everett的相对态表述便以多世界诠释的新名称开始广为人知。 随着人们对多世界诠释的兴趣不断增长,Everett准备重新回到物理学界对量子理论中的测量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不幸的是,他于1982年死于心脏病。
可想而知,霍金先生是多世界诠释理论的最积极鼓吹者之一,因为现在薛定谔的猫,不管它是死是活,尽可以藏匿在它自己喜欢的世界里面。当然,霍金先生也可以不必去充当虐杀动物的凶手了。其实,多世界诠释理论在大多数弦理论家、量子引力和量子宇宙学家中都极受欢迎,相信它的著名物理学家除了霍金之外,还有费曼、盖尔曼和温伯格等,这三位都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自然,也不是所有的物理学家都看好多世界诠释理论的。与霍金先生共同建立奇点理论的彭罗斯 (Roger Penrose)先生就是最坚决的反对者之一。
1997年8月,在美国马里兰大学(UMBC)举行的量子力学讨论会上,国际上最权威的物理学家们对他们所认可的量子力学解释进行了投票表决,结果是: 哥本哈根诠释 13票 、多世界诠释 8票 、其他诠释 18票。1999年7月,在剑桥的牛顿研究所有更多物理权威参加,结果如下:哥本哈根诠释 4票 、多世界诠释 30票 、其他诠释 50票。很多物理学家认为正统的哥本哈根解释已成昔日黄花,多世界诠释是目前最好的解释,但并不意味着它就是绝对正确的解释。
再回过来说霍金先生放出的那句狠话吧,其实他是套用了纳粹帝国的空军元帅戈林先生的名言“一听到‘文化’这个词,我就打开我勃朗宁(著名的手枪品牌)上的保险机!” (Wenn ich Kultur höre, entsichere ich meinen Browning!)。戈林先生为何如此痛恨文化呢?这与他的童年教育有关。对于戈林影响最大的人是他的教父Hermann von Epenstein,这是一个轻视文化道德、崇尚金钱权力的人,他的言行在年幼的戈林心中留下了终生难灭的印象。1905年,当戈林12岁时就被送到Ansbach的一所寄宿学校读书。普鲁士学校的那种刻板传统的教育方式,使戈林无法忍受。3年后,他逃学回到了Veldenstein的老家。这一段学校生活在戈林心中种下了仇视文化的种子,回家过了一段时间,老戈林将他送到Karlsruhe的一所士官学校,戈林发现这才是适合他去的地方。除了戈林,纳粹帝国的第二号元首赫斯先生也经常喜欢说这句话。追本溯源,这句话最早是德国纳粹剧作家兼诗人Hanns Johst在他写的一个剧本《斯拉格特》(Schlageter)第一幕中的一句台词。A.L.斯拉格特(1894-1923)本人是普鲁士自由军团(Freikorps)成员,被希特勒尊为纳粹的烈士形象。
写写又跑题了,看来真是有点控制不住键盘了。不过,结束前我还想再饶几句舌。
还是回到当年念硕士那会儿。读了那篇“Schrödingers Katze”后,我们班上也组织过一次以“薛定谔的猫”为主题的小型研讨会。那时大家刚开始学习量子力学,拥有的知识都很局限,认识也较肤浅,讨论浮于泛泛的哲学层面,未能深入到量子力学的本质。大体上可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持批判态度,认为哥本哈根学派关于猫的死和活取决于观察是贝克莱主教“存在就是被感知”在量子力学领域中的翻版;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哥本哈根学派是量子力学的正统,对于原子及亚原子粒子行为的解释是合理的,但有待于完善。我还记得赞成前一种观点的章君曾提出“纵然在微观尺度上存在着两种相反而并存的状态,宏观世界是否也遵循这种叠加原理呢?”当时班上没人能回答他的疑问。(认真想想,我到现在都无法回答这一问题。)章君65年进清华,文革中跟随蒯司令冲冲杀杀,在井冈山内很有点小名气。来分院读研究生时还有专案人员找他外调过“三种人”的情况。毕业后他去德州大学阿灵敦分校念PhD,旋即又转赴芝加哥大学读MBA。章君后来开办了一家实业公司,频频往返于大陆和北美,生意很成功。不幸九十年代末在上海莘庄死于车祸,才刚刚过知天命之年。赞成后一种观点的主要是谭君。谭君77年与他的孪生兄弟从随父母下放的苏北沭阳同时考进复旦,成为当地的一段佳话,大二那年又越级考上研究生。谭君的博士是在德国达姆城工业技术大学念的,后来又去莫斯科大学做博士后。现在任职北京中科院,从事纳米技术的开发研究。
注释
[1]其它的物理学佯谬有阿喀琉斯的乌龟、麦克斯韦的妖精、拉普拉斯的惡魔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双生子。
[2]对任何线性系统,在给定地点与时间,由两个或多个刺激产生的合成反应是由每个刺激单独产生的反应之和。这种过程称之为叠加。
[3]一个力学量能取的数值是其算符的全部本征值,本征函数所描写的状态称为该算符的本征态。
PS,
暑假结束,今天开始上班,以后不太会有时间再撰写长篇文字了。且把以前做过的扎记整理成篇,贴在《独立评论》上,以答谢一些同网的厚爱。
断章师爷 2009-08-17
断章师爷
上个月断断续续下了好几周雨,走过书架,总似乎闻到些幽幽的霉尘气。眼下骄阳炎炎。 小区内的左邻右舍都倾巢而出, 男女老幼皆躺在草地上享受日光。放眼望去,绿茵地上,彩伞林立,玉体横陈。不禁想起《世说新语》中西晋参军郝隆先生“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郝隆先生的书都装在肚里,所谓是“满腹经纶” ;我的书都插在架上,所以是“胸无点墨”。倘若我的所有书籍也象郝隆先生一样藏在肚中,那该多方便啊!只消挺着个鼓鼓囊囊的大肚子,潇洒地走到草地上,仰天八叉地在那儿躺上一阵,所有的霉菌和蠹鱼保管一扫而光。算了,还是回到我的书架边上来吧。
我的书架上有不少旧书,其中一册《科技德语文献》,是那种16开本的讲义,用蜡纸打字后翻印的,装订也很马虎。那还是我读硕士时修第二外语的参考资料。这本纸页泛黄的老讲义看是不会再去看了,却总舍不得扔掉,常会拿在手里摸挲一番,回想一下当年读此书时的情景,这大概也算是一种怀旧吧。
其实,这册外表不中看的讲义汇集了不少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等领域中的名家名篇,物理学方面的就有普朗克的演讲“Religion und Naturwissenschaft”(宗教和自然科学)、海森堡接受巴伐里亚天主教科学院奖时的发言“Wissenschaftliche wahrheit und Religion wahrheit”(科学真理和宗教真理)、泡利的书信“Wolfgang Pauli und C. G. Jung. Ein Briefwechsel”(泡利和容格的通信)等。第一篇“Schrödingers Katze”(薛定谔的猫)是从薛定谔发表在《自然科学》杂志上的那篇著名论文“Die gegenwärtige Situation in der Quantenmechanik”(量子力学的现状)中摘录下来的。
凡是读过物理学的人都知道薛定谔方程是量子力学的基本方程,其重要性就像牛顿定律在经典力学中的地位一样。 不过,话得说回来,薛定谔方程再重要,对之感兴趣的人毕竟只限于物理学圈内;薛定谔先生的那只猫却远远比薛定谔方程更惹人注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薛定谔先生这只半死不活的猫把物理学界闹得人仰马翻,直到现在还不得安宁。
薛定谔先生的猫是物理学史上有名的悖论(或者雅驯些称为佯谬)之一[1],他设计了一个思维实验(Gedankenexperiment):将一只猫关在钢制的密室中,室内还置有一小块放射性元素、一个盛有氰氢酸的玻璃瓶,以及一套受盖革计数器触发控制的、由锤子构成的执行机构。放射性元素不稳定,它会衰变放出一个中子,就此引发了相因的连锁反应,最终结果是锤子打破了室内的那个毒气瓶。事情很明显:如果放射性元素衰变了,那么毒气瓶就被打破,猫就被毒死;要是放射性元素没有衰变,那么猫就好好地活着。
根据哥本哈根学派的量子理论,没有测量之前,粒子的状态是模糊不清的, 取决于各种可能性的叠加结果[2]。(顺便插一句,量子态的叠加性和相干性正是未来的量子计算机和现行的经典计算机之间的根本差别。)也就是说未经测量的放射性元素处于衰变和不衰变这两种状态的叠加,只有确实地测量后才能随机地选择其中一种状态出现。原子核的衰变是随机事件,物理学家能精确测定的只是半衰期¾¾即放射性元素衰变一半所需要的时间。假定放射性元素的半衰期是一天,则过了一天,该元素就少了一半,再过一天,就又少了剩下的一半。但是物理学家却无法知道,放射性元素在什么时候衰变:上午,还是下午?当然,物理学家知道它在上午或下午衰变的几率¾¾也就是猫在上午或者下午死亡的几率大小。
即使不打开密室的门,根据日常的生活经验也可以断定,猫或者是死,或者是活,用量子力学术语来说这是猫的两种本征态[3]。如果用薛定谔方程来描述,猫处于一种死与活的叠加状态。只有在打开密室门的瞬间,才能确切地知道猫究竟是死还是活。这时表征猫的状态的波函数由叠加态立即收缩到某一个本征态,称之为波函数的“坍缩”(Kollaps)。
哥本哈根学派对于几率的诠释是:出现的结果只可能是唯一的一个,但是出现一个结果的前提是波函数必需坍缩。这儿想简单介绍一下何谓坍缩。一般来说,一个物理体系不会处于它的任何一个可观察量的本征态上。但是假如我们测量一个可观察量的话,其波函数就会立刻处于这个可观察量的本征态上。换句话说,某个体系与外界发生某些作用后,它的波函数会发生突变,变成为其中一个本征态或有限个具有相同本征值的本征态的线性组合。这个过程被称为波函数的坍缩。借助于Dirac符号,这一过程的数学表示非常简洁:一个用右矢(ket)表示的包含众多元素(本征态)的波函数仅相当于只含其中某一个元素(本征态)的右矢。但是波函数坍缩的真实性并没有被完全地确定;物理学家一直在争论,波函数的坍缩究竟是这个世界的自然现象之一,还仅仅只是属于某个现象的一个部份而已。为此,物理学家们不得不接受哥本哈根学派的诠释。这样做的代价是违反了薛定谔方程。这就难怪薛定谔先生一直耿耿于怀了。他挖苦说:“按照量子力学的解释,密室中的猫处于“死/活叠加态”——既死了又活着!要等到打开密室看猫一眼才决定其生死。”这儿薛定谔先生使用的动词不是发现(finden)而是决定(entscheiden),可见猫的命运竟然取决于人的观察!
对于物理学家来说,薛定谔先生囚禁猫的那个密室相当于潘多拉的盒子,释放出来的是永不消逝的灾难。一只活蹦乱跳的猫被关进密室后,既不能死,又不能活¾¾这显然是个悖论。数学计算的结果是二者的概率相等,也就是说这两种状态存在的可能性相同。那我们只能宣称此猫不死不活,或者又死又活。严谨的物理学世界被这只猫搅得周天寒彻,精确的物理科学成了一场猜谜游戏。难怪许多物理学家对此怒气冲冲,认为这只寻死觅活的猫简直亵读了科学的神圣。伟大的爱因斯坦先生对于薛定谔的猫也并不待见,他不承认薛定谔先生的猫的非本征态之说。因为他深信“上帝是不会掷骰子的”,认为一定有一个内在的机制组成了事物的真实本性。他花了数年时间企图设计一个思维实验来检验这种内在真实性是否在起作用,遗憾的是他没有完成这种设计就去世了。
正当物理学家们被薛定谔先生这只猫的死活折磨得苦不堪言时,薛定谔先生本人却挥一挥衣袖,悄悄地离开了密室中的猫,转而从科学的角度去思考生命的本质,很快写出了不朽的名著 《什么是生命?》(Was ist Leben? )。在薛定谔先生阐述生命的奥秘时,被他囚禁在密室中的猫依然生死不明。然而,物理学家们一如既往地为薛定谔先生这只猫困惑、愤怒甚至憎恨,以至于希望这只该死的猫“像恐怖电影那样从视线中消失”。
但是这只恶魔附身的猫并未因此消逝,在这个充满困惑的大千世界中留下不少足迹。薛定谔的猫几乎成了娱乐明星,常常和巴甫洛夫的狗作为搭档一唱一和地出现在剧本、音乐和漫画中。最露脸的那次大概是被《恐惧之泪》(Tears of Fears)这个80年代红极一时的乐队作为一首歌的标题进行演唱,尽管唱词是“薛定谔的猫在这个世界中死了” (Schrödingers cat is dead to the world)。
当然物理学世界,更是薛定谔的猫经常出没的场所。本世纪初,根据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J. R. Friedman等人在接近绝对零度的超导体环形电路中由几十亿对电子构成的超导流的实验中,两个宏观不同的磁通态分别相当于“死猫”和“活猫”,它们在环中反向流动形成的对称和反对称的叠加相当于一只由“死”和“活”叠加的薛定谔猫。与薛定谔最初设计的单个粒子相比,几十亿对电子绝对是天文数字,所以著名的《Nature》 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报导,标题是《薛定谔的猫现在胖了》(Schrödinger's cat is now fat)。2005年底,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所的D. Leibfried等人在《Nature》杂志上称,他们使6个铍离子在50微秒内同时顺时针自旋和逆时针自旋,实现了两种相反量子态的等量叠加纠缠,也就是“薛定谔猫”态。在量子计算中把一种与所有处于0的量子比特(qubit)和所有处于1的量子比特的叠加相同的状态称之为猫态。用数学式来表示,即所有元素为0的右矢与所有元素为1的右矢的加和。据有关专家称,“薛定谔猫”态不仅具有理论研究意义,也有实际应用的潜力。比如,多粒子的“薛定谔猫”态系统可以作为未来高容错量子计算机的核心部件,也可以用来制造极其灵敏的传感器以及原子钟、干涉仪等精密测量装备。
身残志坚的斯蒂芬•霍金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地坐着轮椅遨游在不见天日的黑洞中,孜孜不倦地探索着宇宙起源的奥秘。他试图合并量子理论与广义相对论,期望以此解释整个宇宙从诞生到演化的过程。但是薛定谔先生的这只猫始终是量子理论上空一片飘忽不去的乌云,时不时会扰得霍金先生心神不定。以致霍金先生在不少场合中咒骂过“一听到薛定谔的猫,我就去拿我的枪” (When I hear of Schrödinger's cat, I reach for my gun.)。当然罗,即使把枪交给霍金先生,他也无法扣动扳机,因为他周身上下只有大脑和一个手指可以活动。更好的办法,是找个场所将这只该死的猫藏匿起来。
话分两支,1957年普林斯顿大学一个不出名的研究生Hugh Everett III公布了一个他创立的理论。他假设所有孤立系统的演化都遵循薛定谔方程,波函数不会坍缩,而量子的测量却只能得到处于叠加态的一种结果。Everett认为测量仪器与被测系统的状态之间有某种关联,称之为相对态。Everett表示,根据他的理论,测量带来的不是波函数的坍缩,而是一个分裂(Splitting)的宇宙。宇宙像一个阿米巴虫,当电子通过双缝后,虫子自我裂变,成为两只几乎一模一样的变形虫。唯一的不同是,一只虫子记得电子从左而过,另一只虫子记得电子从右而过。这样,薛定谔的猫再也不必为死活问题困扰,宇宙分裂成了两个,一个有活猫,一个有死猫。遗憾的是,整个物理学界对Everett的相对态异常冷漠。1959年Everett飞去哥本哈根叩见玻尔,后者却不作任何评论。心灰意冷的 Everett 退出物理界,任职于国防部五角大厦,后来又创办Lambda公司,成了一名资产亿万的私营承包商。
然而,冷灰中爆出了热栗子。1968年北卡州大学的量子权威Bryce S. DeWitt对 Everett 的假说给出了更为清晰的表述。DeWitt认为在测量过程中,由初始波函数描述的世界分裂为许多个相互不可观察但同样真实的世界分支,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对应于整个系统叠加态中的一个确定的成员态。这样,Everett的相对态表述便以多世界诠释的新名称开始广为人知。 随着人们对多世界诠释的兴趣不断增长,Everett准备重新回到物理学界对量子理论中的测量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不幸的是,他于1982年死于心脏病。
可想而知,霍金先生是多世界诠释理论的最积极鼓吹者之一,因为现在薛定谔的猫,不管它是死是活,尽可以藏匿在它自己喜欢的世界里面。当然,霍金先生也可以不必去充当虐杀动物的凶手了。其实,多世界诠释理论在大多数弦理论家、量子引力和量子宇宙学家中都极受欢迎,相信它的著名物理学家除了霍金之外,还有费曼、盖尔曼和温伯格等,这三位都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自然,也不是所有的物理学家都看好多世界诠释理论的。与霍金先生共同建立奇点理论的彭罗斯 (Roger Penrose)先生就是最坚决的反对者之一。
1997年8月,在美国马里兰大学(UMBC)举行的量子力学讨论会上,国际上最权威的物理学家们对他们所认可的量子力学解释进行了投票表决,结果是: 哥本哈根诠释 13票 、多世界诠释 8票 、其他诠释 18票。1999年7月,在剑桥的牛顿研究所有更多物理权威参加,结果如下:哥本哈根诠释 4票 、多世界诠释 30票 、其他诠释 50票。很多物理学家认为正统的哥本哈根解释已成昔日黄花,多世界诠释是目前最好的解释,但并不意味着它就是绝对正确的解释。
再回过来说霍金先生放出的那句狠话吧,其实他是套用了纳粹帝国的空军元帅戈林先生的名言“一听到‘文化’这个词,我就打开我勃朗宁(著名的手枪品牌)上的保险机!” (Wenn ich Kultur höre, entsichere ich meinen Browning!)。戈林先生为何如此痛恨文化呢?这与他的童年教育有关。对于戈林影响最大的人是他的教父Hermann von Epenstein,这是一个轻视文化道德、崇尚金钱权力的人,他的言行在年幼的戈林心中留下了终生难灭的印象。1905年,当戈林12岁时就被送到Ansbach的一所寄宿学校读书。普鲁士学校的那种刻板传统的教育方式,使戈林无法忍受。3年后,他逃学回到了Veldenstein的老家。这一段学校生活在戈林心中种下了仇视文化的种子,回家过了一段时间,老戈林将他送到Karlsruhe的一所士官学校,戈林发现这才是适合他去的地方。除了戈林,纳粹帝国的第二号元首赫斯先生也经常喜欢说这句话。追本溯源,这句话最早是德国纳粹剧作家兼诗人Hanns Johst在他写的一个剧本《斯拉格特》(Schlageter)第一幕中的一句台词。A.L.斯拉格特(1894-1923)本人是普鲁士自由军团(Freikorps)成员,被希特勒尊为纳粹的烈士形象。
写写又跑题了,看来真是有点控制不住键盘了。不过,结束前我还想再饶几句舌。
还是回到当年念硕士那会儿。读了那篇“Schrödingers Katze”后,我们班上也组织过一次以“薛定谔的猫”为主题的小型研讨会。那时大家刚开始学习量子力学,拥有的知识都很局限,认识也较肤浅,讨论浮于泛泛的哲学层面,未能深入到量子力学的本质。大体上可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持批判态度,认为哥本哈根学派关于猫的死和活取决于观察是贝克莱主教“存在就是被感知”在量子力学领域中的翻版;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哥本哈根学派是量子力学的正统,对于原子及亚原子粒子行为的解释是合理的,但有待于完善。我还记得赞成前一种观点的章君曾提出“纵然在微观尺度上存在着两种相反而并存的状态,宏观世界是否也遵循这种叠加原理呢?”当时班上没人能回答他的疑问。(认真想想,我到现在都无法回答这一问题。)章君65年进清华,文革中跟随蒯司令冲冲杀杀,在井冈山内很有点小名气。来分院读研究生时还有专案人员找他外调过“三种人”的情况。毕业后他去德州大学阿灵敦分校念PhD,旋即又转赴芝加哥大学读MBA。章君后来开办了一家实业公司,频频往返于大陆和北美,生意很成功。不幸九十年代末在上海莘庄死于车祸,才刚刚过知天命之年。赞成后一种观点的主要是谭君。谭君77年与他的孪生兄弟从随父母下放的苏北沭阳同时考进复旦,成为当地的一段佳话,大二那年又越级考上研究生。谭君的博士是在德国达姆城工业技术大学念的,后来又去莫斯科大学做博士后。现在任职北京中科院,从事纳米技术的开发研究。
注释
[1]其它的物理学佯谬有阿喀琉斯的乌龟、麦克斯韦的妖精、拉普拉斯的惡魔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双生子。
[2]对任何线性系统,在给定地点与时间,由两个或多个刺激产生的合成反应是由每个刺激单独产生的反应之和。这种过程称之为叠加。
[3]一个力学量能取的数值是其算符的全部本征值,本征函数所描写的状态称为该算符的本征态。
PS,
暑假结束,今天开始上班,以后不太会有时间再撰写长篇文字了。且把以前做过的扎记整理成篇,贴在《独立评论》上,以答谢一些同网的厚爱。
断章师爷 2009-08-17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