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是势能,在原子里也就是-e^2/r。正如sin(x)的函数是连续的但sin(x)=0的解却是不连续的一样,求解薛定谔方程中的E,也将得到一组分立的答案,包含了量子化的特征:整数n
为了描述原子中电子能量不是连续的现象,玻尔强加了“分立能级”的假设,海森堡则运用矩阵导出了这一结果。薛定谔说不用那么复杂,只要把电子看成德布罗意波,用一个波动方程去表示,就行了。他从经典力学的哈密顿-雅可比方程出发,利用变分法和德布罗意公式,求出了一个非相对论的波动方程,用希腊字母ψ来代表波的函数:
△ψ[8(π^2)m/h^2] (E - V)ψ= 0
这便是名震整部20世纪物理史的薛定谔波函数。三角△叫做“拉普拉斯算符”,代表了某种微分运算。h是普朗克常数。E是体系总能量,V是势能,在原子里也就是-e^2/r。正如sin(x)的函数是连续的但sin(x)=0的解却是不连续的一样,求解薛定谔方程中的E,也将得到一组分立的答案,包含了量子化的特征:整数n。电子有着一个内在波频,如同吉他的琴弦:弦的两头是固定的,所以只能形成整数波节。如果波长是20厘米,那么弦长只能是20厘米、40厘米、60厘米……。原子光谱不再为矩阵力学所专美,它同样可以从波动方程中推导出来
也将得到一组分立的答案,包含了量子化的特征:整数n。电子有着一个内在波频,如同吉他的琴弦:弦的两头是固定的,所以只能形成整数波节。如果波长是20厘米,那么弦长只能是20厘米、40厘米、60厘米……。原子光谱不再为矩阵力学所专美,它同样可以从波动方程中推导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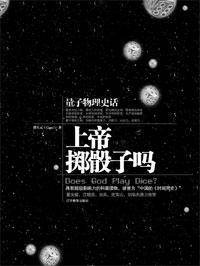
从数学上看,这个函数叫做“本征函数”(Eigenfunction),分立的解叫做“本征值”(Eigenvalue)。所以薛定谔的论文叫做《量子化是本征值问题》。从1926年上半年,他一连发了四篇专题论文,彻底地建立了另一种全新的力学体系——波动力学。他还写了《从微观力学到宏观力学的连续过渡》的论文,证明经典力学只是波动力学的特殊表现.
薛定谔就是不能相信,一种“无法想象”的理论有什么实际意义。而玻尔则坚持认为,图像化的概念是不可能用在量子过程中的。最后,谁也没有被对方说服。
晚会台上放了个锁着的箱子,上面的标签是“薛定谔方程ψ”。
“女士们先生们,”主持人宣布,“谁先猜出箱子里藏的是什么——就能得到晚会的最高荣誉。”
下面顿时七嘴八舌:“能量?频率?速度?距离?时间?电荷?质量?”
“好。”主持人满意地说,“我提示一下,这个ψ是一个连续不断的东西。”
既然是连续不断,那么那些量子化的条件就都排除了。比如电子的能级不是连续的,肯定不是ψ。
“另外,ψ是个没有量纲的函数,但它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每一个电子,在一个虚拟的空间里云彩般地扩展开去。这种扩散及其演化都是经典的,连续的,确定的。”
这时宝箱的发现者薛定谔站了起来:“很明显,ψ是一个空间分布函数。当它和电子电荷相乘,就代表电荷的空间实际分布。电子是一团波,像云彩一般地向每一个方向延伸扩展,变成无数振动的叠加。我们听够了奇谈怪论,诸如电子像跳蚤一般地在原子里跳来跳去,还有那故弄玄虚的矩阵,没人知道它的物理含义。回到坚实的土地上来吧。简洁、优美、直观、连续,这是物理学的胜利之杖。”
“嗯,薛定谔先生”,波恩站起来说,“虽然这是您找到的,但您有没有真正地打开过箱子看看?”
这令薛定谔大大地尴尬:“说实话,没有。那么,你说这箱子里是……?”
波恩神秘地笑了:“我猜,这里面藏的是……骰子。”
可以想象,当波恩于1926年7月将骰子带进物理学后,引起了何等的轩然大波。可怜的波恩直到28年后,才因为这一杰出的发现而获得诺贝尔奖——比他的学生们晚上许多。
波恩认为,ψ,准确的说是ψ的平方,代表了电子在某个地点出现的“概率”。电子不会像波那样扩散,但它的出现概率则像一个波,严格地按照ψ的分布所展开
武侠味的科学史,物理和物理学家那点事。读《上帝掷骰子吗?量子物理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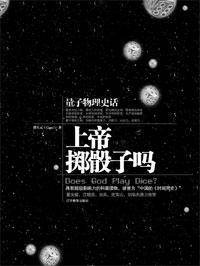
读点:全书概要整理
笔记整理/佚名
玻尔模型有着鲜明的量子化特点。电子只能处于一些“特定的”能量状态中,称为定态。电子可在不同态之间转换,即跃迁。从E2跃迁到E1,这并不表示电子经历了E2和E1两个能量之间的任何状态,而是从原先轨道上消失,神秘地出现另一条轨道上。
对于拥有众多电子的重元素来说,为什么它的一些电子能够长期地占据外层电子轨道,而不会落到近核的低轨道上?泡利在1925年做出了解答:没有两个电子能够享有同样的状态,而一个轨道有着一定的容量。当电子填满了一个轨道后,其他电子便无法再加入到这个轨道中来。
德布罗意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赋予电子一个基本性质,让它们自觉地表现出种种周期和量子化现象。根据爱因斯坦方程,如果电子质量m,那么它有个内禀的能量E = mc^2。同时E = hν,电子一定会有内禀的振动频率ν= mc^2/h。当电子以速度v0前进时,必定伴随着一个速度为c^2/v0的波……波速远超光速,但德布罗意证明这种波不携带实际的能量和信息,因此并不违反相对论。爱因斯坦只是说,没有一种能量信号的传递能超过光速。德布罗意把这种波称为“相波”(phase wave),后人又称“德布罗意波”。波长等于速度除以它的频率,λ= (c^2/v0 ) / ( mc^2/h) = h/mv0。
1923年,德布罗意求出相波之前,正是康普顿携光子说解释康普顿效应、带领微粒大举反攻之时。朗之万出于挽救失足青年的良好愿望,将德布罗意的论文交给爱因斯坦点评。谁料爱因斯坦马上予以了高度评价。整个物理学界这才开始全面关注德布罗意的工作。证据,证据!如果电子是一个波,那就把它的衍射实验做出来。
捕捉电子位置的仪器也早就有了,电子在感应屏上总是激发出一个小亮点。哪怕是电子组成衍射图案,它还是一个一个亮点的堆积。如果电子是波,理论上单个电子就能构成整个图案,只不过非常黯淡而已。可事实是,只有大量电子的出现,才逐渐显示出衍射图案来。
无论微粒还是波动,都没能在“德布罗意事变”中捞到实质性好处。波动对光电效应、康普顿效应束手无策,而微粒也还是无法解释双缝干涉。光子、电子、α粒子、还有更多的基本粒子也纷纷出战。战争全面升级。现在的问题是,这整个物质世界到底是粒子还是波。
玻尔在1924年联合克莱默(Kramers)、斯雷特(Slater)发表了BKS理论,尝试同时从波和粒子的角度去解释能量转换,但这次调停成了外交上的彻底失败,不久就被实验所否决。
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1901年出生于维尔兹堡(Würzburg),他很小就在数学和物理方面展示出天才,但同时也对宗教、文学和哲学表现出强烈兴趣。这预示着他以后不仅仅将成为一个划时代的物理学家,同时也将成为一名为重要的哲学家。
回到泡利1925年提出的“不相容原理”吧。原子大厦里每间房都有4位数的门牌,其每一位都代表了电子的一个量子数。当时3个量子数已知,第四个则众说纷纭。克罗尼格(Ralph Kronig)把它看成电子自旋,但遭到海森堡和泡利一致反对。因为这样就又回到了一种图像化的电子小球概念,违背了从观察和数学出发的本意了,再说也违反相对论——它的表面转速高于光速。
1925年秋,自旋假设又在荷兰莱顿大学的两个学生乌仑贝克(George Eugene Uhlenbeck)和古德施密特(Somul Abraham Goudsmit)那里死灰复燃。导师埃仑费斯特(Paul Ehrenfest)虽无把握,但建议两人先发表。老资格的洛仑兹应邀帮他们算了算,结果电子表面的速度达到了10倍光速。两人风急火燎地要求撤销短文,但埃仑费斯特早就给Nature杂志寄了出去。
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玻尔首先表示赞同,海森堡通过计算也转变了态度。美国物理学家托马斯发现光速问题上人们都犯了一个计算错误。很快海森堡和约尔当用矩阵力学处理了自旋,大获全胜。
然而,泡利一直对自旋深恶痛绝。电子已经在数学当中被充分表达了——现在什么形状、轨道、大小、旋转等种种经验性的概念又幽灵般地回来了。原子系统比任何时候都像个太阳系,本来只有公转,现在连自转都有了。某种意义上泡利是对的,电子自旋不能想象成行星自转,它具有1/2的量子数,转两圈才露出同一个面孔,这里面的意义只能由数学来把握。后来泡利真的从特定的矩阵出发推出了这一性质,而一切又被狄拉克于1928年统统包含于他那相对论化了的量子体系中。
不久海森堡又指出了解决有着两个电子的原子——氦原子的道路,使得新体系再次超越了玻尔的老系统。量子的力量现在已经完全苏醒了,接下来的3年间,它将改变物理学的一切。
为了描述原子中电子能量不是连续的现象,玻尔强加了“分立能级”的假设,海森堡则运用矩阵导出了这一结果。薛定谔说不用那么复杂,只要把电子看成德布罗意波,用一个波动方程去表示,就行了。他从经典力学的哈密顿-雅可比方程出发,利用变分法和德布罗意公式,求出了一个非相对论的波动方程,用希腊字母ψ来代表波的函数:
△ψ[8(π^2)m/h^2] (E - V)ψ= 0
这便是名震整部20世纪物理史的薛定谔波函数。三角△叫做“拉普拉斯算符”,代表了某种微分运算。h是普朗克常数。E是体系总能量,V是势能,在原子里也就是-e^2/r。正如sin(x)的函数是连续的但sin(x)=0的解却是不连续的一样,求解薛定谔方程中的E,也将得到一组分立的答案,包含了量子化的特征:整数n。电子有着一个内在波频,如同吉他的琴弦:弦的两头是固定的,所以只能形成整数波节。如果波长是20厘米,那么弦长只能是20厘米、40厘米、60厘米……。原子光谱不再为矩阵力学所专美,它同样可以从波动方程中推导出来。
从数学上看,这个函数叫做“本征函数”(Eigenfunction),分立的解叫做“本征值”(Eigenvalue)。所以薛定谔的论文叫做《量子化是本征值问题》。从1926年上半年,他一连发了四篇专题论文,彻底地建立了另一种全新的力学体系——波动力学。他还写了《从微观力学到宏观力学的连续过渡》的论文,证明经典力学只是波动力学的特殊表现.
薛定谔就是不能相信,一种“无法想象”的理论有什么实际意义。而玻尔则坚持认为,图像化的概念是不可能用在量子过程中的。最后,谁也没有被对方说服。
晚会台上放了个锁着的箱子,上面的标签是“薛定谔方程ψ”。
“女士们先生们,”主持人宣布,“谁先猜出箱子里藏的是什么——就能得到晚会的最高荣誉。”
下面顿时七嘴八舌:“能量?频率?速度?距离?时间?电荷?质量?”
“好。”主持人满意地说,“我提示一下,这个ψ是一个连续不断的东西。”
既然是连续不断,那么那些量子化的条件就都排除了。比如电子的能级不是连续的,肯定不是ψ。
“另外,ψ是个没有量纲的函数,但它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每一个电子,在一个虚拟的空间里云彩般地扩展开去。这种扩散及其演化都是经典的,连续的,确定的。”
这时宝箱的发现者薛定谔站了起来:“很明显,ψ是一个空间分布函数。当它和电子电荷相乘,就代表电荷的空间实际分布。电子是一团波,像云彩一般地向每一个方向延伸扩展,变成无数振动的叠加。我们听够了奇谈怪论,诸如电子像跳蚤一般地在原子里跳来跳去,还有那故弄玄虚的矩阵,没人知道它的物理含义。回到坚实的土地上来吧。简洁、优美、直观、连续,这是物理学的胜利之杖。”
“嗯,薛定谔先生”,波恩站起来说,“虽然这是您找到的,但您有没有真正地打开过箱子看看?”
这令薛定谔大大地尴尬:“说实话,没有。那么,你说这箱子里是……?”
波恩神秘地笑了:“我猜,这里面藏的是……骰子。”
可以想象,当波恩于1926年7月将骰子带进物理学后,引起了何等的轩然大波。可怜的波恩直到28年后,才因为这一杰出的发现而获得诺贝尔奖——比他的学生们晚上许多。
波恩认为,ψ,准确的说是ψ的平方,代表了电子在某个地点出现的“概率”。电子不会像波那样扩散,但它的出现概率则像一个波,严格地按照ψ的分布所展开。
让我们来做一个思维实验。想象一台仪器每次只发射出一个电子,穿过双缝打到感光屏上激发出亮点。一个电子只会留下一个点。电子出现在屏幕上的什么地方完全不是一个确定的过程。但它出现频率高的地方,恰恰是波动干涉条纹的亮处,出现频率低的地方则对应于暗处。每一个电子的行为都是随机的,但随机分布的总模式却是确定的,表现为干涉条纹图案。单个电子不会如薛定谔所言在屏幕上打出一滩图案。
但是,这不是对于经典决定论物理学的大不敬吗?对于任何系统,只要给出足够初始信息,赋予足够的运算能力,就能够推算出这个体系的一切历史和未来。哪怕骰子,告知骰子的大小、质量、质地、初速度、高度、角度、空气阻力、桌子摩擦系数等一切情报,就可以理论上计算出骰子将会掷出几点来。决定论(determinism)是物理学家心中深深的信仰。19世纪初,法国的大科学家拉普拉斯(Pierre Simon de Laplace)用牛顿方程计算出行星轨道后展示给拿破仑看。拿破仑问:“在你的理论中,上帝在哪儿呢?”拉普拉斯平静地回答:“陛下,我的理论不需要这个假设。”
可是现在有人说,物理从理论上也无法预测电子行为,只能找到电子出现的概率而已。这种不确定不是因为信息不足或者计算能力不足而引起的,它是物理定律本身的属性。这是对整个决定论系统乃至整个自然科学基础的挑战。
然而,第二天早上,玻尔的胜利便到来了。玻尔指出:怎么测量△m呢?用一个弹簧称,假设指针位移△q,箱子也就在引力场中移动了△q,根据广义相对论红移效应,原子频率变低等效于时间变慢△T。可算出△T>h/△mc^2,代以质能公式△E=△mc^2,则得到△T△E > h,正是海森堡测不准关系!假如准确测量△m或△E,就根本没法控制光子逃出的时间T!
现在轮到爱因斯坦说不出话来了。光箱实验非但没能击倒量子论,反而成了它最好的证明。无论如何,因果关系不能抛弃!爱因斯坦的信念此时几乎变成一种信仰了。不久他又提出一个新的实验,玻尔得第三次接招了。
想象一个大粒子衰变成两个小粒子反向飞开。如果粒子A自旋为“左”,粒子B便一定是“右”,以保持总体守恒。在观察之前,它们的状态是不确定的,只有一个波函数可以描绘它们。彼此飞离数光年后,我们开始观察粒子A,它的波函数坍缩了,瞬间随机选择了比如说“左”旋。此时粒子B也必须瞬间成为 “右”旋了。B是如何得知A的状态呢?难道有超光速信号来回于它们之间?这显然违背了相对论。
玻尔再次化解了这次攻击。爱因斯坦不言而喻地假定两个粒子在观察前分别具有两个“客观”自旋状态。但在玻尔看来,观测之前“两个”粒子无论相隔多远,仍然是一个整体!或说,“两个独立”的粒子是不存在的,只有“一个粒子”,无需传递什么信号。观测的瞬间,“两个”粒子才变成实在。EPR佯谬最多表明了,在“经典实在观”看来量子论是不完备的,这简直是废话。
自我意识!
把一个原子和一只猫放在一个暗箱中。每当原子衰变而放出一个中子,就通过相关装置激发一连串反应,最终打破箱子里的一个毒气瓶。如果原子衰变了,那么猫就被毒死。反之,猫就好好活着。在观察之前,原子处在衰变/不衰变的叠加状态,那么猫呢,难道处于又死/又活的混合状态?
薛定谔把量子效应放大到了日常世界。推广开来,当我们不去观察的时候,世间万物都是处于“存在/不存在”的不确定性状态。当我们闭眼时,月亮是不存在的?贝克莱(George Berkeley)主教的名言:“存在就是被感知”(拉丁文:Esse Est Percipi)轰然响起。好歹贝克莱还认为事物客观地存在的,因为“上帝”在看着一切。而量子论?“陛下,我不需要上帝这个假设”。
如果猫能说话,它会描述这种既死既活的感觉吗?猫当然不会说话,可如果箱子里的是人呢?他肯定坚定地宣称,自己从头到尾活得好好的,因为他自己已经是一个观察者了!问题是猫也在不停观察自己啊。难道区别就在于一个可以反驳另一个只能“喵喵”叫吗?令人吃惊的是,这的确可能是至关重要的分别!人有猫所没有的东西,那就是“自我意识”!
关于“意识”我们下文再论。但无论如何,“薛定谔的猫”,追随着芝诺的乌龟、拉普拉斯的预言家、麦克斯韦的妖精、爱因斯坦的双生子,走进了科学史上怪异形象的名人堂。
现在我们来认识一下现代计算机的奠基人之一、20世纪最杰出的数学天才——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传说他6岁就能心算8位数乘法,8岁懂得微积分,10岁通晓5种语言,12岁精通泛函分析。无论这些传说是否真实,但他的成就是板上钉钉的:从集合论到数学基础,从算子环到遍历理论,从博弈论到数值分析,从计算机结构到自动机理论,每一项都足以彪炳史册。下面谈的是他在量子学中的贡献。
1926年,冯诺伊曼在哥廷根担任大数学家希尔伯特的助手,再加上诺戴姆,三人共同发表了论文《量子力学基础》,将希尔伯特算子理论引入量子论中,将这一物理体系从数学上严格化。1932年,他又出版了名著《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书中冯诺伊曼证明了几个关于测量行为的结论,深深影响了一代物理学家对波函数坍缩的看法。
“坍缩”的内在的机制一直不太清楚。是“观测”吗?但“观测”一词的精确定义是什么?冯诺伊曼指出,测量仪器本身也由粒子组成,拥有自己的波函数。观测对象因仪器的观测而坍缩并变得确定,但不确定性的叠加状态实际上已经传到了仪器上。无论加入多少仪器,链条的最后一台仪器总处在不确定状态。假如把测量仪器算进整个系统,那么大系统的波函数从未彻底坍缩过!
然而当我们看到仪器报告的确定结果后,坍缩过程显然结束。大脑接受到测量的信息后,波函数不再捣乱了。难道说,人类意识(Consciousness)的参予才是波函数坍缩的原因?在诺伊曼看来,波函数可以看作希尔伯特空间中的一个矢量,而“坍缩”则是它在某个方向上的投影。然而,难道是人类意识造成了这种投影?换句话说,一只没有自我意识的猫可以陷于死/活的混合态中,人类则不然!长久以来,自然科学将“主观”逐出地盘,现在量子理论又把它大摇大摆地请了回来!
物理学需要“意识”?这是本世纪最大的笑话!但说这话的人竟是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尤金?维格纳(Eugene Wigner)于1902年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他是冯诺伊曼中学时的学长、狄拉克的大舅子。他把群论应用到量子力学中,和狄拉克、约尔当等人一起成为量子场论的奠基人。他参予了曼哈顿计划,在核反应理论方面有突出贡献。1963年,他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奖金。
维格纳捅了一个比薛定谔的猫更大的马蜂窝——“维格纳的朋友”。
这位爱猫的“维格纳的朋友”,戴着防毒面具和猫一起进了箱子。箱外的维格纳猜测他的朋友正处于(活猫高兴)AND(死猫悲伤)的混合态。可事后那位朋友肯定会否认这一叠加状态。维格纳总结道,当朋友的意识包含在整个系统中的时候,叠加态就不适用了。箱子里的波函数因为朋友的观测而不断地被触动,因此只有活猫或者死猫两个纯态的可能。维格纳论证说,既然外界变化可以引起意识改变,意识反作用于外界使波函数坍缩是不足为奇的。他把论文命名为《对于灵肉问题的评论》(Remarks on the mind-body question),收集在他1967年的论文集里。
总之,如果不在终点处插入半反射镜,光子就沿着某一条道路而来,反之它就同时经过两条道路。但是否在终点插入反射镜,可以在光子通过了第一块半反射镜之后、到达终点之前才决定——在事情发生后再来决定它应该怎样发生!这是哥本哈根派的一个正统推论!在光子上路之前还是途中来做出决定,这在量子实验中没有区别。历史不是确定和实在的——除非它已经被记录下来。更精确地说,光子在通过第一块透镜到我们插入第二块透镜这之间“到底”在哪里,是一个无意义问题。5年后,马里兰大学的卡洛尔?阿雷(Carroll O Alley)和其同事做了延迟实验,验证了这一看法。与此同时慕尼黑大学也作出了类似结果。
宇宙由一个有意识的观测者创造出来也不再荒谬。宇宙的漫长演化直到被一个智能生物所观察才成为确定。观测参予了创生!这就是所谓的“参予性宇宙”模型(The Prticipatory Universe)。这实际上是增强版的“人择原理”(anthropic principle):我们存在这个事实本身,决定了宇宙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它必须使得智能生物存在并发问“宇宙为什么是这样的?”。可以想象:各种宇宙常数先是不确定的叠加,只有被观测后才变成确定。但必须保持在某些精确范围内,以便令观测者有可能存在并观察它们!这似乎是一个逻辑循环:我们选择宇宙,宇宙创造我们。这又叫“自指”或者“自激活”(self-exciting)。
在经典双缝困境中,如果不去观测,电子应同时通过两条缝。此时它的波函数是一个线性叠加,按照薛定谔方程演化(即|ψ>可以表示为:a|通过左缝> + b|通过右缝>),数学家彭罗斯称之为“U过程”,它是确定的、严格的、经典的、可逆(时间对称)过程。不管U过程如何发展,系统始终保持线性叠加。
一旦观测电子,电子波函数“坍缩”,只剩下|左>或者|右>中的一个态。这个过程按照概率随机发生,不再可逆,彭罗斯称之为“R过程”。哥本哈根派认为“观测者”引发了这一过程,极端派扯上“意识”。
MWI则认为,根本没有所谓“坍缩”,R过程从未发生!任何时刻、任何孤立系统的波函数都按照U过程演化!所谓孤立系统是一个理想状态,我们在现实中唯一能找到的例子,显然,正是宇宙本身!宇宙这个极为复杂的波函数,包含了许多互不干涉的“子世界”。宇宙的整体态矢量是全体子矢量的叠加和,每一个子矢量都是在某个“子世界”中的投影,代表了薛定谔方程一个可能解。“子世界”彼此垂直正交,不能相互干涉。
因此,宇宙态矢量本身始终按照薛定谔方程演化。只有一个“宇宙”,但它包含了——而不是“分裂”成了——多个“世界”!“坍缩”不过是投影在某个世界里的“我们”因为身在此山中而产生的想法罢了。所有的“世界”都发生在同一个时空中,只不过因为互相正交而无法彼此交流罢了。
MWI最大的功绩就是把“观测者”从物理中一脚踢开,不必再为奇迹般的“坍缩”伤脑筋。薛定谔猫摆脱了又死又活的煎熬,自得其乐地一死一活在两个不同世界中。大自然又可以自己做主了,不必在“观测者”的阴影下苟延残喘,直到某个拥有“意识”的主人赏了一次“观测”才得以变成现实。这样一幅客观的景象还是符合大部分科学家的传统口味的,至少不会像哥本哈根派那样让人抓狂。经典决定论复活了,因为薛定谔方程是决定性的。给定了某个时刻t的状态,就可以从正反两个方向推演出系统任意时刻的状态。时间的“流逝”不过是种错觉!上帝不再掷骰子了。
显然,多宇宙和哥本哈根在这里出现了根本的不同:假设每隔一秒钟发射一个光子到半镀镜来触动机关。哥本哈根预言,就算运气极佳,你也最多听到几声“咔”后听见一声“砰”然后死掉。但多宇宙预言:永远都会有一个“你”活着。只要你坐在枪口面前,你永远只会听到一秒响一次的“咔”,永远不死(虽然在别的数目惊人的世界中,你已经尸横遍野,但那些世界对你没有意义)!但只要你从枪口移开,你就又会听到“砰”声了,因为这些世界重新对你恢复了意义。
所以对箱中人而言,假如他一直听到“咔”而活着,那么多宇宙解释多半是正确的。假如他死掉了,那么哥本哈根解释就是正确的,但可笑的是,这种正确对他来说也没有意义了,人都死掉了。
困惑出现了。枪一直“咔”是一个极小的概率啊(连续响n次“咔”的概率是1/2^n)?怎么能说对你而言枪“必定”会一直连响下去呢?
关键在于,“对你而言”的前提是,“你”必须存在!
一个相关的例子可以帮助理解这个概率问题:从任一男性,比如你,开始往上溯,那么他爸爸有儿子、他爷爷有儿子、他曾祖父有儿子……可以一直上溯到人类的诞生!而反过来想,不管历史上冰川严寒、洪水猛兽、兵荒马乱、饥饿贫瘠,这个连续的“生男孩”链条始终不断,似乎是个非常小的概率(如果你是女性,可以往娘家那条路上推)。但假如因此感慨说,你的存在是一个百万年不遇的“奇迹”,就非常可笑了。显然,你能感慨的前提是你的存在本身!一个家族n代都有儿子的概率极小,但对你我这样的男人来说,却是“必然”的,概率为100%的!同理,有智慧生物的宇宙产生的概率是如此低,但按照人择原理,宇宙必须如此!而在量子自杀实验中,只要你始终存在,那么对你来说枪就必须100%地不发射!
但可惜的是:就算箱子中的你发现了多宇宙解释是正确的,这也只是对你本人而言的知识。就箱外旁观者而言,事实永远都是一样的:你在若干次“咔”后被一枪打死。旁观者依然要围着你的尸体争论,到底是按照哥本哈根你已彻底从宇宙中消失了,还是按照MWI你仍然在某个世界中活着。而你也永远不能从那个世界来到我们这里,告诉我们多宇宙论是正确的!
这就是所谓的“量子永生”(quantum immortality)。如果你举枪自杀,总存在着至少一种可能:子弹粒子流穿过你脑袋粒子团而不发生任何破坏作用,你依然活着。而根据多宇宙理论,一切可能的都是必然的。你总会在某个世界中活着。自杀之外的任何例子都是这样。因此,一旦一个“意识”开始存在,从它自身的角度来看,它就必定永生!这就是最强版本人择原理,也称“最终人择原理”。
可恶的“意识”又出现了。如果所谓活着意味着连续的“意识”,但“意识”是如何“连续存在”的根本就没有经过考察。假如“意识”必定会在某些宇宙中连续地存在,那么应该断定它不但始终存在,而且永远“连续”,不该有“失去意识”的时候(例如睡觉或者昏迷)。不过也许的确存在一些世界我们永不睡觉,谁知道呢?再说暂时沉睡后又苏醒,这对于“意识”来说好像不能算作“无意义”。更重要的,如何定义在多世界中的“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总之,这里面逻辑怪圈层出不穷,而且几乎没什么可以为实践所检验,都是空对空。也不太有人为了检验哥本哈根和MWI而实际上真的去尝试!因为实验的结果只有你自己知道而已,你无法把它告诉别人。而且要是哥本哈根解释不幸地是正确的,那你也就呜乎哀哉了。而且就算你在枪口前总是不死,你也无法确实地判定这是因为多世界的正确,还是仅仅因为你的运气非常非常非常好。你最多能说:“我有99.999999..99%的把握宣称,多世界是正确的。”
回到1927年第五届索尔维会议吧,德布罗意讲述了他的“导波”理论。他想象,电子是实在的粒子,但的确受到时时伴随着的那个波的影响,这个波就像盲人的导航犬,指引它如何运动。德布罗意的理论完全是确定和实在论的。量子效应表面上的随机性是由一些不可知的变量所造成的,把它们考虑进去,整个系统是确定和可预测的,符合严格因果关系。这样的理论称为“隐变量理论”(Hidden Variable Theory)。
玻姆把所谓的“导波”换成了“量子势”(quantum potential)概念。根据他的理论,粒子不论何时都具有确定的位置和动量,以及,“量子势”——类似波动的东西,它按照薛定谔方程发展,在电子周围扩散。量子势效应和它的强度无关,只和它的形状有关,这使它可以一直延伸到宇宙的尽头而不衰减。量子势场使粒子每时每刻都对周围环境了如指掌,比如感应到双缝的存在或其中一条缝的被关闭,再比如同测量仪器发生作用并导致电子本身发生微妙变化。这种变化是不可预测的,因为主宰它们的是一些无法直接探测到的“隐变量”。
玻姆体系基本做到了传统量子力学所能做到的一切!但量子力学一路走来,诸大师为它打造了金光闪闪的基本数学形式。它漂亮、简洁、实用,似乎没有理由给它强迫加上笨重丑陋的附加假设。玻姆隐函数理论复杂繁琐、难以服众。他假设电子具有确定轨迹,又规定因为隐变量的扰动而观察不到这样的轨迹!这无疑违反了奥卡姆剃刀原则。难道为了世界的实在性,就非要放弃物理原理的优美、明晰和简洁吗?事实上,爱因斯坦,甚至德布罗意,生前都没有对玻姆的理论表示过积极认同。
更关键的是,玻姆放弃了一样重要的东西:定域性(Locality)——即不能有超距作用的因果关系,任何信息必须以光速为上限而发送!玻姆的量子势可瞬间把触角伸到宇宙尽头,违反了相对论的精神。
回到双缝电子问题——|电子>=|穿过左缝>+|穿过右缝>
按照标准哥本哈根解释,电子没有一个确定的位置,它同时又在这里又在那里!
按照MWI,这是一种两个世界的叠加。
按照隐变量,假如考虑了隐变量,就能确实地知道电子究竟通过了左边还是右边。
系综解释则比较圆滑:“叠加”违背常识,是不对的。不可观察的隐变量也太过火。实验结果的纯随机性不可否认,它已经传达了世界的本质:“电子=左+右”的时候,并非指一个单独的电子同时处于左和右两个态,而指许多电子50%通过左边,50%通过右边。所谓“单个电子通过了哪里”的问题,没有物理意义!不过这是否是掩耳盗铃?假如我想知道我的寿限,巫师却告诉我这个城市平均寿命是70岁,而我一个人的寿命没什么意义!
系综解释是保守和现实主义的,它保留了量子论全部数学形式,而在哲学领域试图靠耍小聪明来逃避形而上探讨。把搞不清楚的划为“没有意义”也许很方便,但正是这类问题使得科学变得迷人!
像猫这样大的系统,每秒必定有成千上万的粒子经历了这种过程。因为整个系统中的粒子是互相纠缠的,少数几个粒子的自发定域会造成多米诺效应。结果整个宏观系统会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一次整体上的自发定域。一个含有1摩尔粒子的系统(数量级在10^23个)只要0.1微秒就会发生定域。这里既不需要“观测者”,也不牵涉到“意识”,它只是随机过程!果真如此,那么薛定谔猫的确经历了死/活叠加,但只维持了非常短时间,然后马上“自发”精确化,变成单纯的非死即活。这听上去不错,该理论解释了微观上的量子叠加和宏观上物体的不可叠加性。
量子论的基本形式只是一个框架,描述单粒子运动。但要描述高能情况下多粒子的相互作用时,必定要涉及到场,这需要如同普朗克把能量量子化一样,把麦克斯韦电磁场也量子化——建立量子场论(quantum field theory)。
这一工作由狄拉克开始,经由约尔当、海森堡、泡利和维格纳的发展。所有粒子都是某种场,有着不同的能量形态。能量最低时就是真空,真空不过是粒子的一种不同形态(基态)而已,任何粒子都可以从中被创造或互相湮灭。狄拉克方程预言“反物质”的存在。某种粒子和其反粒子相遇,就放出大量辐射,然后双方同时消失,其关系符合E=mc^2。最早的“反电子”由加州理工的安德森(Carl Anderson)于1932年在研究宇宙射线的时候发现。此事意义异常重要,仅过了4年安德森就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麻烦很快到来。1947年《物理评论》刊登了兰姆移位和电子磁矩的实验结果,和理论发生了微小偏差。人们利用微扰办法来重新计算,但越是求全的加入所有微扰项后,计算结果适得其反地总是发散为无穷大!最后的解决方案是日本物理学家朝永振一郎、美国人施温格(Julian S Schwiger)和戴森(Freeman Dyson),还有费因曼所分别独立完成的所谓“重正化”(renormalization)方法。虽然认为重正化牵强的科学家大有人在,但这种手段把无穷大赶走后,剩下的结果准确得令人瞠目结舌:量子电动力学(QED)经过重正化修正后,在电子磁距计算中与实验值符合到小数点之后第11位——这是物理学当时的世界纪录。朝永振一郎,施温格和费因曼也分享了65年诺贝尔物理奖。最近彭罗斯声称,对赫尔斯-泰勒脉冲星系统的观测积累起了确凿的引力波存在的证明,使广义相对论的精度和实验吻合到10的负14次方,超越了QED(赫尔斯和泰勒获得93年诺贝尔物理奖)。
标准薛定谔方程是非相对论化的,没有考虑光速上限。而这一工作最终由狄拉克完成,最后完成的量子场论是量子力学和狭义相对论的联合产物。只考虑电磁场,得到量子电动力学。量子电动力学认为,电磁力意味着两个粒子间不停交换光子。想象两个相互面对的溜冰者不停把一只光子皮球传来传去,必定越离越远,表现为斥力。同性相吸就是两人背靠站立,把球扔到对方面对的墙壁上再反弹到对方手里。
但处理原子核内事务时,就不再是电磁力了。氦原子核由两个质子和两个中子组成。中子不带电,可两个质子都带正电却没有互相弹开,此处万有引力微弱得可以忽略不计,必有一种比电磁力更强大的核力,叫做强相互作用力。相对应地,弱作用力是造成不稳定粒子衰变的原因。这样,宇宙中共有着4种力:引力、电磁力、强相互作用力和弱相互作用力。
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认为,强相互作用是因为核子交换一种新粒子——介子(meson)而形成的。安德森发现了介子,现称μ子,和汤川理论无关。汤川预言的那种介子现称π子,由1947年为英国人鲍威尔(Cecil Frank Powell)发现。汤川获得49年诺贝尔物理奖,次年是鲍威尔。
那些感受强相互作用力的核子称为“强子”,如质子、中子。64年盖尔曼提出所有强子都可进一步分割,即今天家喻户晓的“夸克”。每个质子或中子由3个夸克组成,每种夸克有不同的“味道”和“颜色”,通过所谓的“量子色动力学”(QCD)来描述。夸克间同样交换粒子来作用,称为“胶子”(gluon)。
弱相互作用交换的粒子称为“中间玻色子”。弱相互作用力的理论形式同电磁力很相似,它们是同一的么?特别是李政道与杨振宁提出弱作用下宇称不守恒后,这一怀疑愈加强烈。终于,60年代,美国人格拉肖(Sheldon Glashow)、温伯格(Steven Weinberg)和巴基斯坦人萨拉姆(Aldus Salam)证实了这一怀疑,他们的成果称作“弱电统一理论”,3人得到了79年诺贝尔奖。该理论预言的3种中间玻色子(W+,W-和Z0)到了80年代被全部发现。
弱作用力和电磁力已经合并了,下一个目标是强相互作用力,这块地域目前被量子色动力学所统治。但两国君主多少有点血缘关系——都是在量子场论的框架下。三者统一的理论被称为“大统一理论”(Grand Unified Theory,GUT),它来发展出了多个变种,不同变种预言了不同的现象,但迄今为止这些现象都还没被确凿证实。
“大统一”的称号是名不副实的。如果4种力其实都是同一的呢?那样一来,整个自然,整个物理就四海归一,任何人都无法抗拒这种诱人景象。物理学家们早把眼光放到了引力身上,即使他们连强作用力也仍未最终征服,可谓尚未得陇,便已望蜀。量子论终于迎来了一个最强大的对手——广义相对论。
引力和其他3种力似乎有本质不同——它总是吸引的!如果说电磁力、强作用力和弱作用力勉强算同文同种,引力则傲然不群。何况它的国王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量子场论虽然争取到了狭义相对论的合作,但还是难以征服广义相对论。这里凸现了量子论和相对论的内在矛盾,必定要经历一场艰难困苦,才能最后完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宏愿。只有这样的理论才真正称得上“大统一”。不过既然大统一的名字已被GUT占用,这种终极理论有了另一个名字:万能理论(Theory of Everything,TOE)。
本来在超弦中有无穷多种对称性可供选择,两人发现只在极有限的对称形态中,才得以消除这些反常而自洽。筛选下来的那些群还可包容规范场理论及标准粒子模型。伟大的胜利!“第一次超弦革命”由此爆发,物理界倾注出罕见的热情和关注。
|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